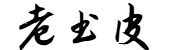《禁忌寝事》by甜脆萝卜
laoshupi 2025-08-09 09:48 10 浏览
这里的寝是(因病)卧床、躺在床上的意思。题目中问到的这句话出自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刘向所作的国别体史书《战国策》,这是其中《赵策》里面的内容,故事发生在赵武灵王开始进行胡服骑射的历史背景之下。题目中的这句话是公子成对赵武灵王所说的,大意是说我早该来拜见您,但因为我“不佞寝疾,不能趋走”,意思就是说卧病在床,行动不便。由此可见,这里寝的意思是(因病)卧床、躺在床上。
意思是睡不着觉。形容心事重重。出自《战国策·齐策五》。
成语出处
《战国策·齐策五》:“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成语辨析
【近义词】:寝不聊寐
成语用法
作谓语、定语;是用于人的心情
示例
玄德因思水镜之言,寝不成寐。 ★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三十五回。
夜不能寐、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辗转反侧,寝不安席
“食无味,寝无眠”的意思是:吃饭吃的没有什么味道,睡觉难以入眠天天失眠。
“食无味,寝无眠”《论语-卫灵公》:食无味,寝无眠,秋叶黄。鬓沾白,今日辉煌,他日沦陷。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释义:食:吃饭;寝:睡觉;虑:考虑,顾虑;忧:忧愁,忧患。
译文:
吃什么食物都感到没有味道,睡觉睡得难以入眠,秋天树叶已经开始变得枯黄。头发两鬓已经变白了,也许今天的生活是很辉煌的,但是终有一天会沦陷。人若没有了长远的打算,以后一定会被眼前的难事所困扰。
这句话告诉我们,人无论在何时何地,无论是辉煌还是失意的时候一定要有长远规划,要考虑大局,不可只看眼前的事物。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出现眼前的忧患。表示看事做事应该有远大的眼光,周密的考虑。
扩展资料:
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就是一种因果循环。今日因是他日果,今天不为他日做打算,他日成今日时必然有许多忧虑,不容不作努力。
再深入思索,就会令人豁然开朗。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应该是指,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忧愁),是肇因于以前没有深思熟虑的作为;同样的,今天的作为如果未经长远的深思熟虑,未来必会尝到苦果。
所以,这句话除了提醒我们要深谋“远虑”,还点出一个要点:凡事必是“自作自受”,这是每个人都要有的认知。
重新品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除了警惕自己、要对今日的事物深思熟虑、深度思考外,还应对将来进行作打算,即所谓的“深谋远虑”。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古老的谚语,充满了先人的智慧,告诫人们要未雨绸缪,不要老看眼前的事物,而忘却了人之所以积极奋斗的远景期待。
夜里睡觉睡不着。失眠了
相关推荐
- 总裁媳妇爱上我_我的总裁女友
-
这个看你的抉择了。和总裁媳妇玩,犹如玩火!玩好了,瞬间精彩。玩砸了,万劫不复,先想想清楚哈。容颜易老,三思而后行,切记!切记!他其实早就爱上杨辰了不过他要求让杨辰跟所有的情人断绝联系才一直僵持...
- 童话歌词_夜之童话歌词
-
光良的《童话》第一句是:忘了有多久 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这首歌在制作时,音乐统筹光良与陈建良特别找来了日本歌手森山直太朗的编曲制作人TaichiNakamura来为这首歌编曲...
- 轩辕剑之天之痕电视剧免费观看
-
结局一:小雪结局 在最终决战后,小雪没有发动失却之阵,玉儿身死。 触发条件:于小雪的隐藏好感度高于拓跋玉儿。 在游戏中各种选项中选择偏向小雪的选项即可,不需要达到多少好感度,只需要高于玉儿就可以...
- 简然_简然什么意思
-
卷一百七十八,出处宋史,行简然之没有。女主简然是一个单身多年的小白领,没事就去相亲,不过经常失败。本来简然已不报什么希望,但这次她遇到了秦越,也就是我们的男主,本以为自己嫁的是一个普通男人,谁料老公藏...
- 原来我是高人啊_原来我是高人啊免费阅读
-
就叫《我真不是盖世高人》,该小说的作者是归心,小说从头到尾情节精彩,压抑一直围绕着读者的心情,符合大神级小说一贯的作风,喜欢此类题材的读者们可千万不能错过了。身为穿越者的李凡,自然渴望修仙,他曾经去过...
- 最强神医混花都全文免费阅读
-
《最强神医混花都》是阿雷创作的一部都市异术超能小说,讲述了主角林萧作为神医的唯一传人,回归花都的故事。在他的生活中,各路美女环绕,他同时成为了这些美女的贴身保镖。此外,林萧还以他神奇的医术纵横花都,拯...
-
- 《绾青丝》_《绾青丝》百度云
-
我想首先可能是云峥的缘故吧,云峥成为了一个不可超越的形象。还有男猪脚男配角把好男人各种类型都包罗进去了,受众群会就会庞大,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再次,可能这篇小说写的挺早的缘故,那个时候大家看的好文不多,所以当然的绾青丝自然成了个中翘楚,就像...
-
2025-09-19 03:21 laoshupi
- 快穿之反派boss又黑化了_快穿之反派boss又黑化了by南浔
-
推荐两本1.书名:《我养的反派都挂了》作者:墨书白小短评:得寸进尺厚脸皮吃货颜狗女主vs隐忍深情忠犬男主,虐男主/前世今生,每个世界的反派都是同一个人,每个世界都在虐男主,最虐的是前1-5个世...
- 少将请您回家_少将请回家博君一肖的背景故事
-
、帝王:待我君临天下,许你四海为家;2、国臣:待我了无牵挂,许你浪迹天涯;3、将军:待我半生戎马,许你共话桑麻;4、书生:待我功成名达,许你花前月下;5、侠客:待我名满华夏,许你当歌纵马;6、琴师:待...
- 她不乖小说免费阅读_她不乖小说免费阅读全文
-
沈悠的小说:《妃要逃跑,皇上,我不好吃》男猪脚有一个专门记女猪脚“错误”的木质本子:她(季语涵女主)可以假装杀(闹着玩的,不是真杀)了他(端木离男主),之后把端木离绑起来,她就是老大,就不用...
- 蜜汁炖鱿鱼电视剧免费完整版
-
蜜汁炖鱿鱼其实是一套系列丛书,总共有三部曲,分别是《神之左手》、《蜜汁炖鱿鱼》和《密室困鱿鱼》。这部作品题材新颖,爱情故事吸引人,被奉为经典。原著中的女主角外号“鱿鱼殿下”,正好与书名中的鱿鱼相呼应。...
- 择天记小说免费_择天记小说免费听书
-
《择天记》是中国内地网络小说作家猫腻所创作的长篇玄幻小说,于2014年5月28日开始连载于创世中文网,2017年5月4日完结。作品讲述了在人妖魔共存的架空世界里,陈长生为了逆天改命,带着一纸婚书来到神...
- 不败战神杨辰更新最快1724章
-
不败战神杨辰一天更新三章杨辰秦惜不败战神小说更新最快到第1678章。《不败神婿》又名《不败战神》,作者:笑傲余生,分类:都市言情,状态:连载中。文案:青年本名杨辰,入伍仅仅五年,便立下汗马功劳,功勋卓...
- 云顶天宫40集全集免费观看_云顶天宫在线观看免费观看21集
-
一、先来排列下盗墓笔记正确的总体观看顺序:1、先看《盗墓笔记》正文部分:分别是七星鲁王宫、西沙海底墓、秦岭神树、云顶天宫、蛇沼鬼蜮、谜海归巢、阴山古楼、邛笼石影。然后再去看盗墓笔记大结局上下;2、其次...
- 重生之异能狂妻txt下载_重生之异能狂妻全文txt
-
《重生之异能狂妻蓝修》是一部非常受欢迎的小说,其中主角蓝修的经典语录也备受读者喜爱。她的话语充满了智慧和力量,让人们感到鼓舞和启发。例如,“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终点。”这句话告诉...
- 一周热门
- 最近发表
- 标签列表
-